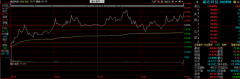42岁丧夫51岁入狱52岁女儿自杀人生一波三折她却活到94岁
1987年,一位鹤发苍颜的华裔老妇人,端坐在一家书店专门为了摆放的典雅书桌前,正在给排着长队的人们,签名售书。
看到来到跟前的热心读者,她总是抬起头,冲着对方微微一笑,然后在书籍的扉页上写上好她的英文名字,然后非常礼貌地用布满着皱纹的双手将书托起,递送至读者手里。
这位优雅的老妇人,此时已经72岁,她正在签售的书名翻译过来为《上海生死劫》,这是她一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,而且一写就是一部长篇巨制。

她并非专业作家,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篇自传式小说作品,也是她人生中唯一一部长篇作品,一经出版后,不仅在美国火爆热销,而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,热遍全球。
这种赞誉并非仅针对她的出身,而是对她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态度,在经历了悲惨的人生之后,郑念依旧能够让内心充满着坚强,并向生活展露出坦然的微笑。
祖父姚晋圻,不仅曾中过清朝的会试,而且还被皇帝纳入过翰林院,成为一名庶吉士,这个职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,却代表着学问与才识。
而处于从清朝向民国时期过渡阶段的父亲姚秋武,在清末的时候,被公派到日本留学,所学专业是海军军事领域,学成之后未能为清朝所用,却成了民国政府的海军将领,最高军衔曾达到海军少将级别,可谓位高权重。

高贵的出身与优渥的家境,让郑念从小便培养出带有中国传统贵族气息的优雅气质,及至少女时期,与其他权贵豪门出身的大小姐相比,她身上的特质极为与众不同。
民国时期,剧烈的时局与社会变革,带来了新旧文化与思想的激烈碰撞,每个人的身上都会留下时代的烙印,特别是当时的年轻女子。
当时许多权贵与富家大族,他们的思想并未随着时代而改变,仍旧固守着以前的观念与生活态度,甚至怀念并留恋着清朝时期,心中仍残留着辫子。
这种人家的小姐,即便不再裹起小脚,心中的三纲五常思想却根深蒂固,她们也会受到良好的教育,只是,这种教育是旧式的,多是些《女经》、《孝经》、《烈女传》之类的东西。

也有许多家境良好的女子,因为祖辈与父辈思想的开明,她们则完全摆脱了旧有的风气,甚至一股脑地全部接受了不断涌进来的新思想、新观念。
这些大家小姐,她们所受的教育是纯新式、纯西方的,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,本着舍弃的态度,一律予以否定。
她们无论从外在的打扮、着装,还是行为与生活方式,以及思想与观念,便是连所喜好的文化与艺术,皆是西式的、洋化的、开放的。
她因为家庭从旧时代延展过来的关系,一半的身子踩在旧文化、旧思想之中,一半的身子却又探入到新文化、新思想里面。

正是因为两种文化、两种思想,在她身上的碰撞与结合,让郑念浑身散发着中国新时代女性特有的气质与韵味。
把她放在旧式女子中,她身上会闪着耀眼的独立而自信的光芒;把她放在新潮女子中,她又可以低眉含笑,仿佛中国工笔画中走出来的摇着团扇的优雅仕女。
正如当年比较开明的其他权贵豪门之家的小姐一样,郑念先是在国内读了一阵子燕京大学,1930年,在她15岁的时候,便在父亲的安排下前往英国留学。
来到英国的郑念,并没有豪门大小姐的做派,在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,她开始了完全的自主与独立,从中国的贵族小姐回归到了一个平民学生的生活。
父亲姚秋武在临别之际,曾一再嘱咐她要自强自立,用心学习:“新时代与旧时代不同,女子也要独立,自己掌握人生,而不是依附他人,为此,你此次去英,务必专注学业,这是你以后可以获得独立的根本。”
正是带着父亲的嘱托与期望,郑念在学业上十分的专注,经过几年的苦修之后,她获得了经济学的硕士学位。

郑念的美貌与气质,让在英国的她博得了许多同时期留学生的青睐,身边的追求者一直持续不断,而且,当年的这些留英学生,很大一部分在国内的家境都不错,也不乏一些名门之后。
但郑念对于这些追求者一概采用了直接拒绝的方式,在这方面,她的表现非常的西化,没有任何的委婉与含蓄,她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:“我们并不合适,况且我来英国的目的,是完成学业,而非恋爱结婚。”
郑念并不是口是心非,她的内心也是这么想的,父亲的嘱咐言犹在耳,她对自己的要求是,一定要专注于学业,至于男女之情与婚姻之事,不急。
经人介绍得知,郑康褀正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,之所以能够吸引郑念的注意,并让她的内心荡起丝丝的涟漪,不只在于郑康褀俊美的长相,更在于他有着中国旧书生的儒雅气质,以及中西融汇的知识。

郑康褀与郑念在某些方面几乎完全相同,都有一些旧式的中化,也有着新式的西化,两个似乎有些矛盾的特质,却完美地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。
在郑念眼中,如果只是一个旧时代穿着长袍的书生,满嘴的之乎者也,她是不会喜欢的;如果只是一个身装西装,到处宣扬着新文化、新思想,一提起中国传统文化,即完全嗤之以鼻,她也是不会喜欢的。
准确地说,他是一个从旧时代走出来,却又能融入新时代的男人,这让他在更倾向于全洋化的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中,显得如此卓尔不群。
两人因为相互吸引,再加上身上异国的留英学生们经常举办一些聚会活动,也为两人提供了很好的彼此靠近的机会。

一度有曾经的追求者拿着郑念以往的台词开起了玩笑:“你当初不是说自己要专心学业,恋爱婚姻一事并不会考虑吗?如今遇到看对眼的,便把以前的说法都忘记了。”
郑念略带羞色地嗔道:“倘若不是你的出现,也不会破了我的誓言,现在好了,在这些人眼中,我已经是个口是心非、言而无信之人了。”
郑念不敢马上答应,因为她骨子里还是有些旧思想的,总觉得要先征求父亲的同意才好,于是,便以书信的方式,洋洋洒洒地将她与郑康褀的关系与情况,仔仔细细地告知了父亲。
好在父亲十分开明,再加上郑康褀的家庭出身也算不错,有才有貌,两人又是自由恋爱,走到婚姻这步,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原本答应父亲要好好完成在英国的经济学学业,以便实现一个新时代女性的独立的郑念,此时却以一个英国留学经济学硕士的高学历,成了紧跟在丈夫身边的全职太太。
其中最为深层的原因,就是郑念一直所保留着的中国旧传统的女性意识;当然,另外一层原因,就是她对爱情的投入,看着要远赴他国工作的郑康褀,她不忍也不舍他一人前去。
这是一个陷入幸福爱情与美满婚姻中的郑念,以一个依赖于丈夫的小女人的身份,对即将前往澳大利亚赴任的郑康褀所做的表白。
1942年,在郑康褀于国外从事外交驻外工作期间,他们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取名为郑梅萍,从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,除了彼此间的恩爱没变,家庭中又因孩子的出生,平添了许多的温馨之情。

1949年,新中国成立之后,党和政府向许多海外的人才伸出的橄榄枝,希望他们能够回国,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贡献自己的才智。
这些心系祖国,满怀爱国情怀的仁人志士,从世界各地纷纷回到了国内,其中就包括郑念与郑康褀夫妇。
回家之后,郑康褀进行政府部门从事他非常熟悉的外交事务工作,而郑念依旧做着她的全职太太,在家中相夫教女。
生活似乎有些变化,又好像没什么变化,两人的感情如同陈年老酒,更加的芬芳馥郁,而唯了的女儿郑梅萍,也出落成了一个美丽大方的少女。

从与郑康褀相识相恋,到结婚生女,再到看着孩子一天天地成长,近20年的时间里,郑念是深感幸福的。
但是,到了1957年的时候,相对于整个漫长的人生,略显得短暂的幸福,却戛然而止,郑念心中那座幸福花园,从繁花锦盛,开始逐渐变得落红满地。
1957年丈夫郑康褀的因病离世,让郑念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,突然失去一生所爱之人,其惶恐之状与悲痛之情令一直优雅的她几度失控。
就在她刚从丧夫之痛中走出来没多久,某天,一群人冲进她布置精致的家中,除了翻箱倒柜地寻找罪证之外,还将她软禁在家中,不允许她外出及会客。

性格刚强的郑念依旧没有被打垮,因为她还有个心理的巨大支撑,就是唯一的女儿郑梅萍,为了女儿,她咬紧牙关也要活下来,走出去。
女儿郑梅萍,已经凭着她姣好的外貌与精到的演技,成为名专业演员,她多么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足够的长,可以多看几场女儿的演出、多看几部女儿的电影。

同时,也为了不让自己出去后,被女儿看出她所受的苦难,不让女儿为她担心,即便在几尺见方的牢房里,她也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。
整整被关了6年之后,1973年,她面带微笑地走出了监狱,她伫立在监狱门外,左顾右盼,希望能看到女儿前来迎接的身影,可一直等到日落,女儿郑梅萍都没有出现。
直到她冲到女儿工作的单位,了解到女儿在她被投入监狱不久,即被人活活打死并扔下楼之后,一向优雅的她却直接委顿于地。
1980年9月27日,郑念带着满心的伤痕,在朋友的帮助上,经由香港辗转来到了美国,并定居下来。

来到美国之后,她每天总是准时起床,精心装扮,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,仿佛丈夫郑康褀与女儿郑梅萍都在身边一样。
郑念每天的生活起居非常简单,在美国她并无亲朋好友,也极少出门,她最常做的事,便是呆坐着书桌前,看着摆在眼前的丈夫与女儿两人的遗像。
直到有一天,她觉然觉得应该要写些什么,在她尚未离世之前,她想把自己与丈夫和女儿的事记录下来,就这样,随着越写越多,并最终汇集成一本自传体小说《上海生死劫》。
郑念被誉为“中国最后一个贵族”,并仅是因为她出身于贵族家庭,更重要的是她无论身处苦难之中,还是经历苦难之后,她却总能保持着坚强、高雅与微笑。

无论是她一个人在家中,还是外出或面对人群,也无论她身上衣服是新是旧,无论首饰是贵重或廉价,她总是把自己装扮得十分整洁,也总让自己的言行那么得体。
当94岁的她躺在病床上弥留之际,她清醒的那一刻,也不忘拿过镜子,拢起额上微乱的发丝,然后带着一丝如春风般的微笑,溘然而逝。